
月亮的貧困
文/米荊玉
“少時不識月”。古詩詞短、硬、孔隙疏漏,留下了解釋的便宜空間。何為“少時”?我的現年就是我的少時。何謂“不識月”?每年對月亮的思考不一樣,每個時代對月亮的看法也不一樣,今是而昨非;漢唐千年以來,月亮是中國詩人的公用WiFi。邊塞的、青樓的、貶官的,一旦看見月亮,就接上了詩興和靈思,源源不斷供應各種WIFI信號:千里共嬋娟、呼作白玉盤、天風吹落樓頭月、只有相隨無別離。脫發也怨它,思鄉也看它,故友也賞它,荷爾蒙和內分泌也為它紊亂。千載以下,月亮替代了母性、友誼、愛情、仕途、文運、家國等多個角色,“明月何曾是兩鄉”——到了2020年,國際口罩友誼也靠它。
很多雅事兒毀于現代人,月亮就是一例。自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留下登月途中糞便壓縮袋之后,對著月亮闡發任何詩興,都有點內急無門的感覺;月下無論是秉燭、焚香、吃蟹、分月餅,仰頭可見那個壓縮袋在玉盤中影影綽綽。李白寫完“對影成三人”,補一句“此處略去壓縮袋三十公斤”。我個人對星座還是持保留態度:別跟我提什么上升星座、下降星座,你就說有沒有阿姆斯特朗的異味得了。
山巔的月亮大概最貼近古人的月亮。去年在嶗山民宿見過一例月光,芳華皎潔,至圓至福,群星岑寂,知趣地為月亮閃出一大片蒼白夜空。那時候工資挺高、領導疏懶、老婆自拍、女兒啾啁,便覺得這月亮太愛人了。外地的月光我見得少,武夷山中月色如厲鬼,峰影崔嵬、林聲莫名,采訪劇組的記者只有我一個,被煙油味的巖茶頂得雙目炯炯,想起白天在湖水中那個半裸暢游的美女,導游說《西游記》開頭悟空躥天的鏡頭就在九曲溪拍的——這月色好冷。就中年人的記憶里來說,月光太冷,記憶的面餅貼不緊、烙不熟,回憶起來只剩朦朧一團,是俯瞰人間的獨眼。
打從電燈出現,現代生活對月亮的侵害就不曾停止。路燈是月光的天敵,夜生活是賞月的對立面,白話文是詠月詩詞的殺手,從汽車到網絡,從電視到手機,從補課到加班,現代生活的每一個步驟都在刻意疏遠月亮。《卑鄙的我》里長鼻子壞蛋偷走了月亮——試問一個月不見月亮你會注意到嗎?月亮幾乎是闌尾、報紙之后又一個多余的代名詞。就算是月餅廠家,又有幾個工人、幾個老板關心月亮呢?除了狼人、吸血鬼,月亮連個惦記的人都沒有。
公元701年出生的李白,公元1992年出生的李佳琦;李白、李佳琦之間六十代的李氏傳承里,至少有55個李家先輩認為“月下寫詩”是件百姓家尋常事。這是一個月亮崇拜貧困的時代,這甚至是一個剝奪感缺乏的時代。從月光照亮的小徑出發,關于詩歌、文學、雅集,關于崇拜、信仰、皈依,都成為奢侈的、不合時宜的東西。我們互相剝奪了他人對月亮的權利和功能,剩下一枚月餅,怎么說呢,皮不同,餡不同,各自不相與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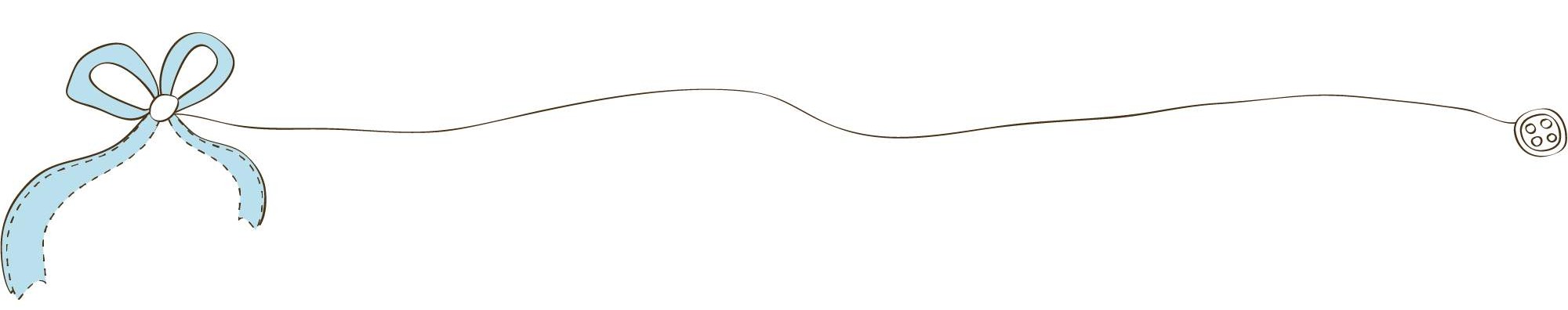

(作者簡介:米荊玉,資深文化記者,山東省作協會員,排骨米飯研究者,發表有《排米人生》《海怪》等作品)

掃碼了解觀海文學社“記憶·中秋”有獎征文詳情

責任編輯:單蓓蓓



